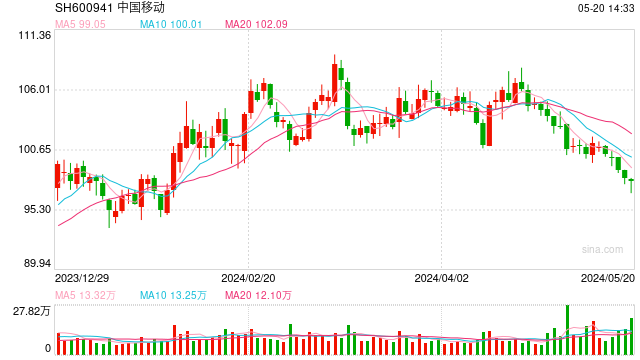在“誰監控了我的手機”的隱私焦慮中,有一道身影較少出現在大眾猜疑鏈里:運營商。
負責移動大數據產品的內部人士,早在五年前寫道:“原先運營商還在探索變現商業模式,現在應該沒有什么秘密可言了,基本上找到了大數據變現的方向。”更直觀的一組數據是,上海數據交易所中,三大運營商的數據產品占比超20%;貴陽大數據交易所里,中國移動的“梧桐風控大數據”產品以超2800次的訪問量遙遙領先。
不過,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點進各大運營商的產品列表,發現了不少讓人頗為意外的交易。
比如中國移動的孕期家庭識別分,輸入電話號碼、姓名、身份證,可輸出對應0~150分值的孕期家庭分數。
多位業內人士表示,識別分是典型的數據交易方式,目的是提供群體篩選結果,無法推測出精確到個人的信息。但運營商內部的業務人員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,他們會約定每個手機號對應的“序列號”,這樣不需要明文傳輸手機號,也能精準交換個人信息。
在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的規定之上,“標簽識別分”等數據產品表面看起來無害健康,但是水面之下,有不少暗箱操作:場外交易不“擦邊”很難拿到銷售業務,“匿名數據”成為皇帝的新衣,個人授權亦無從說起。
上述記者在數據交易所看到的運營商數據產品,名義上都落于風控領域。從業務層面理解,一般是A公司對B公司要求返回的用戶群體進行篩選。
一位負責政企業務的移動內部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解釋,這類數據產品的本質是標簽篩選,交易大致有三步:首先,客戶要根據自身的業務場景制定一個篩選需求,比如需要篩出有辦卡意愿的用戶,并提供用戶資料;隨后,由運營商挑選可靠的數據指標,進行算法或建模分析;最后,通過API接口的方式返回用戶篩選結果。
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,這種“標簽識別分”是一種典型的交易方式,標準化程度高,適合場內交易。
“標簽產品會選擇上架大數據交易中心進行交易,一般會涉及設備ID、手機號等個人信息。”TalkingData總法律顧問兼數據合規官葛夢瑩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解釋,出于安全合規的考慮,實踐中很多企業會在隱私計算平臺中進行數據交互處理,即雙方均上傳自己的加密數據包,做到原始數據不出域、數據可用而不可見。
專門開發風控系統的芯盾時代副總裁杜旭解釋,之所以用這種方式,是因為“識別分”或者“標簽”是平臺挖掘預測的主觀結果,不具備客觀性。此外,如果只看返回的頻率或者統計字段,無法推測出精確到個人的信息。
不過,水面之下的操作方式有很多。
“實際上也有一種交換數據的方式,那就是雙方事先制定一本數據字典。”以杜旭的觀察舉例,在電商公司的數據交換中,雙方可以約定模糊數值對應哪些具體數據,比如識別分為0.8,對應信息為月收入8000~10000元,方便還原更精確的數據。
前述中國移動內部人士還透露了一種常用的“取巧”方法:序列號。由于運營商不能直接提供有具體手機號碼的數據,對待小商客,業務人員往往只會提供群體級別的篩選結果;但遇到大型政企客戶,業務人員會對其提供的用戶手機號碼逐一編號,并用光盤、U盤的形式傳送對應手機號的序列號。此時的群體篩選,搖身一變成了精準查詢。
該移動內部人士還提到,拿“幼兒家庭識別分”來說,如果教育行業的客戶希望篩選一批可能是幼兒家庭的手機號,他們也會組合營銷短信、外呼電話的配套產品一同銷售,可以把篩選人群理解為精準營銷獲客的一環。
從程序上看,客戶的需求是否合規合法,中國移動又能否滿足客戶需求,主要由公司內部的信息安全部把關。不過現實中,運營商的一條明確紅線是不能明文提供手機號、不能提供精確的行動軌跡,至于其他數據交易的顆粒度能有多細——“其實主要還是取決于客戶大小和客情關系。”他坦言。
為什么要用上述方法“包裝”數據,邏輯很簡單:如果數據能精確識別到個人,就落入了個人信息的范疇,需要單獨取得用戶同意,除非數據已經匿名。
但要達到法律意義上的“匿名”沒有那么容易。
一位不愿具名的數據法學者解釋,序列號的這種方式實際上是一種“去標識化”的技術,在不借助額外信息的情況下無法識別到個人,因技術上實現難度低,在企業實踐中更為常見,可以理解為一種弱化版本的“匿名”。
根據我國《個人信息保護》要求,需要滿足無法識別、不能復原兩重標準,才屬于匿名數據。觀韜中茂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吳丹君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,如果能通過序列號重新對應個人手機號,仍然屬于交易個人信息。
按照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規定,交易個人信息前應當向個人進行充分告知,包括交易方的名稱、姓名、聯系方式、處理目的和個人信息的種類,并且需要取得用戶的單獨同意才行。
運營商可能跟哪些第三方交易數據,又是如何取得用戶同意的?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翻閱了三大運營商的個人信息保護政策,幾乎都采用的是一攬子授權。
對于風控查詢,電信和聯通表示,只要用戶合法授權了第三方公司來核驗信息,運營商便可返回個人信息。第三方公司的范圍可以很廣泛,在中國電信的條款里,“金融機構、征信機構、數據服務機構、互聯網企業”都囊括其中。
而對于個性化廣告,移動、聯通承諾除非獲得同意,否則不會跟第三方共享個人信息,但不包括用戶畫像。中國電信使用的是“脫敏信息”一詞:“在收集您的個人信息后,我們將通過技術手段對數據進行去標識化脫敏處理。請您了解并同意,在此情況下我們有權使用已經脫敏的信息。”
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欣此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,個人事先和運營商簽訂的授權文件中的個人信息,和運營商真正調取的個人信息,二者之間存在信息差。用戶未必能夠明白自己的數據用于何處,并真正愿意授權。
對于數據交易雙方,并非不愿意匿名處理,或者沒有意識到有合規風險,難題有二:一方面,實踐中的絕對匿名化難以達到。隨著大數據技術的不斷發展,匿名數據被重新組合、重新定位到個人的風險不斷提高。
另一方面,多位采訪對象都提到了數據產品“大而無用”的流通困境。
前述內部人士透露,在交易過程中,客戶往往需要一些非常精確的個人數據,而一線業務人員背負逐年增長的考核指標,不“擦邊”很難拿到銷售業務,在市縣級存在更多私下數據交易。有些情況下,甚至是公司層面的主動讓步。
“三大運營商越來越卷,只要有一家打破了(隱私)底線,剩下兩家就必須要打破底線,要不然項目不好做。”他無奈地解釋。
根據2023年的財報數據,“通信服務”作為三大運營商的基石,增長速度已經基本持平,幾乎可以一眼望見市場空間的天花板。數據變現,既是借國家數據要素政策的東風,也是運營商營收增長的必選項。
而作為數據下游的風控系統應用方,杜旭解釋,在風控產品的場景中,沒有辦法通過某一單一的數據判斷出風險行為,幾乎都要引進第三方數據綜合判斷。而“原則上說,這種識別分數據產品的輔助權重太小,不足以提供一個決策依據,很難為這種數據產品花錢”。
不愿具名的行業人士表示,監管落地時,最關注的是數據泄露風險,也就是傳輸過程中加密工作有沒有到位。不過多位代理數據合規業務的律師指出,如果進入了司法程序,法院會嚴格按照無法識別、不能復原的雙重標準,審核數據交易的所有環節。
吳丹君感受到了其中兩種利益的拉扯:如果對個人隱私和信息安全的規定過于嚴格,可能會限制數據的自由流通和應用,從而阻礙數據市場的發展活力;相反,如果數據市場的發展缺乏必要的監管,可能會導致個人隱私被忽視。
“長久以來,數據相關行業與隱私安全問題高度綁定,數據隱私保護和數據市場發展之間通常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,監管會根據發展需要,對隱私性和流通性做出一定取舍。”張欣也說。
張欣表示,我國目前是通過“數據二十條”、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《網絡安全法》和《數據安全法》等政策法規設定邊界,引導市場試水。但張欣也坦率指出,目前這些基礎性法律文件,都缺少對數據權屬的明確界定。數據到底屬于誰、能夠享有怎樣的權利,還需等待更明確的法律回應。

VIP課程推薦
APP專享直播
熱門推薦
收起
24小時滾動播報最新的財經資訊和視頻,更多粉絲福利掃描二維碼關注(sinafinance)